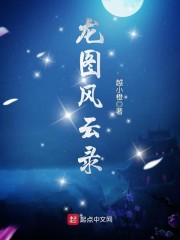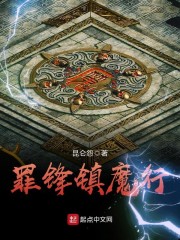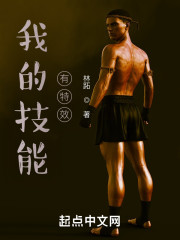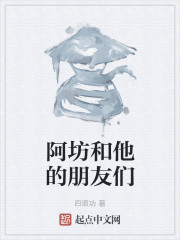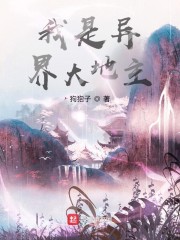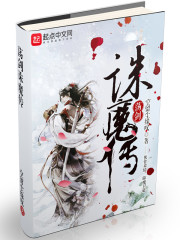三、南越往事(1/3)
南越王朝的都城渚州,城门紧闭。
城内已经宵禁三日,就是白天也严禁进出,更不允许三五聚首窃窃私语。各茶楼酒馆、青楼集市也都关门歇业,往昔车马如龙、人流如织的大街上空无一人,十分的冷清。不时驰过几匹快马,清脆急促的马啼声激荡在街头巷尾,紧张的氛围令人窒息。那是都城的守军正在巡逻,个个神情肃穆,杀气暗隐。
城东的燕子坞巷,是丞相褚庸的府邸,早已五步一哨,十步一岗,戒备森严。两列护卫整装待发,八名轿夫分列在一顶绿尼大轿的左右,大家面无表情,只是静静地等待。
相府的大门突然打开,褚庸在管家的陪同下快步走来。快到轿前,管家褚安疾行几步,把轿帘撩开,褚庸躬腰迅速地钻进轿内。
“去皇宫!”褚安给轿夫吩咐了一声。几个轿夫便各自就位,抬起褚庸就直奔皇宫。清冷的大街透着一股萧煞之气,褚庸心情沉重。南越刚刚安定几年,百姓才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,幸帝就驾鹤西去,确实令人惋惜。
前几年他甫登相位,国库空虚、民生凋敝。就犯难直谏,请求幸帝元昊休生养息,以图国力恢复。幸帝权衡数日,最终同意了他的建议,开始刷新吏治,关注民生。可是南越连年举兵、数度平叛,已致民不聊生、国力锐减。五年来虽然励精图治,奈何积重难返,收效甚微。褚庸始终坚信,政令汤若一以贯之,朝野并能持之以恒,定能国富民强,必成大功。
不过,让褚庸奇怪的是,正在这关键时刻,幸帝竟在三日之前突然驾崩,太子孙烨也在皇上驾崩的当夜离奇失踪。皇上正值壮年,太子也是龙性初成,骤然之间,国君和储君同生变故,这未免太巧了。
这几天宫门紧闭,全城戒严,朝会暂停,群臣居家待召。褚庸虽为百官之首,也对深宫大内这几天发生的巨变一无所知。刚刚宫中来宣,说是萧贵妃召见,令他即刻进宫。在这敏感时刻,杀气暗隐,危机四伏,稍有不慎便可能引来杀身之祸。褚庸知道这其中的凶险,决定察言观色,见机行事。
褚庸隐隐觉得,幸帝元昊突然驾崩、太子孙烨神秘失踪,似乎跟这萧贵妃有关。萧贵妃是萧让之后,萧家的势力在朝廷里盘根错节,门生故吏遍布,历次政权更迭都有萧家的影子。
萧让死后,元正帝孙哲登基,即幸帝之父。为了摆脱萧家的控制,削弱萧家的影响,开始培植新的势力,企图牵制萧家。王家世代为官,是南越颇有影响的名门望族,王清源是族中翘楚,威信极高。此人精明强干、沉稳睿智,元正帝极为器重,屡次提携,官至大司马,参决政事,秉掌枢机。
元和九年,元正帝孙哲亲征闽南,不小心在鄣谷遇伏被流矢射中,生命垂危。临终前将大位传给年方十七的太子元昊,即幸帝,并立王清源之女为皇后,王家的声望从此达到了巅峰。
幸帝深知父王元正帝的良苦用心,延续了元正帝许多的政治主张,对内采取抑萧扬王的对策,即扶持王家来平衡萧家。对外采取合纵连横的外交方略,与各小国交好,共同对付北方强大的大燕。
褚庸听宫中的人传言,太子孙烨之所以早早地被立为储君,并时常被幸帝带在左右,是幸帝和皇后的感情深厚,也是为了报答皇后为保全皇家血脉所付出的惨痛代价。
原来庆光元年,皇后难娩,大人小孩都生死难料,太医们乱成一团,用尽一切办法都难见其效。幸帝焦急万分,当场欲斩杀当值医官,被皇后拼命拦住。皇后为了保全皇家血脉,以身犯险,恳求幸帝下令太医们剖腹。
幸帝悲痛欲绝,心乱如麻,久久下不了这个决心。皇后已经气若游丝,她拉着幸帝的手泪流不止,不断哀求。幸帝不忍,国丈王清源恐再拖不决,母子俱殒。遂当机立断,命令太医剖腹。
太医们只好奉命,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,约摸半柱香的功夫,取出来了一个男婴。这男婴已然浑身青紫,不会啼哭。太医们奋力抢救,终于有了一些生命的迹象,许久才哭出声来。
奈何皇后流血太多,不久便撒手人寰。听说弥留之际,皇后深情地看了看一下孩子,想摸摸他的小脸,却已经无能为力。她望了望幸帝,嘴唇蠕动了几下,想说点什么,也发不出声了,任凭眼角两行眼泪滑落。
幸帝紧握着她的手,心痛如割,当即下召,立这个刚刚出生的男婴为太子,并取名孙烨。听说皇后闻之十分欣慰,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,慢慢才闭上了眼睛。
之后幸帝又陆续取了萧让的孙女萧氏、御史中丞韩佩之女韩氏。萧氏被册封为贵妃,生下了世子裕王靖,裕王靖先天有耳疾,一边的耳朵听不到。韩氏后来封为皇妃,为幸帝生下一男一女,男孩取名孙战,封怀王。女的取名孙姬,封安平公主。这对儿女聪明伶俐,天资过人,尤其是怀王战,深得幸帝喜欢。
太子孙烨名份早定,国之储君身份显贵,宫中上下无不呵护备至。孙烨却不以为然,总是视这些呵护是种羁绊,让他畏手畏脚施展不开,不能随心所欲率性而为。他生性粗犷,行事不拘小节,喜欢追逐嬉闹,经常做些出格的事来。
身边的太监婢女拿他无可奈何,太子自己时常弄的灰头土脸,偶尔摔得鼻青脸肿,幸帝为此常责罚他们。幸帝自己也念及他自幼丧母,身世可怜,对太子比较宽和,常常睁只眼闭只眼,放任他的胡闹。